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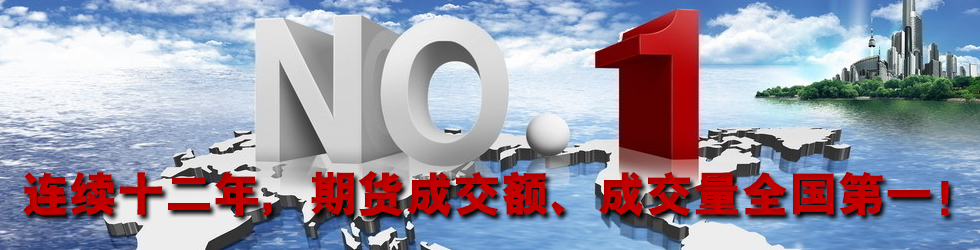 |
 |
人性的弱点:再探金融危机之源
———读EdwardCarr《贪婪与恐惧》有感
人们对金融危机的起因进行了种种剖析——创新过度、监管不足、制度缺陷、应变迟钝……爱德华·卡尔却掘进到更深的人性层面。《贪婪与恐惧》以独特的视角扫描本次金融危机,虽然作者拿不出修复人性的灵丹妙药,但至少为当前风行全球的金融监管改革提供了不少沉重的借鉴,也为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和从业者留下了许多冷静的思考。
金融市场中贪婪和恐惧与生俱来。商品价格上涨主要取决于供需,金融资产的供需比实物商品来得更便捷,因而其价格涨跌可以全凭自身“魅力”。理性投资者牛市中见好就出,熊市中超低不卖,然而这种理性却一次次遭受市场的戏弄。金融市场充满贪婪与恐惧的博弈,成功与失败者的区别仅在于巴菲特所说“当别人贪婪时恐惧,当别人恐惧时贪婪”。理性成功的案例不是没有,但理性失败的案例更多。有了“逆向贪婪与恐惧”的示范效应,在理性增长的同时,贪婪与恐惧也得到超越理性的扩展。投资者无论追求“理性投资”还是修炼“逆向贪婪与恐惧”,无不以赢利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志。
金融市场必须引入投机资本,利用投机创造和保持流动性,达成价值的实现。这也从源头埋下了贪婪与恐惧之根。
拥有两位诺奖得主的对冲基金LTCM演绎了经典案例。LTCM精心在全球发掘不同市场中同类金融资产之不合理价差并从中获利。他们曾敏锐注意到:与30年期国债相比,29年期国债的相对价格低得惊人。而30年期仅比29年期多数月而已。由于很多人不假思索投资30年期国债,无意中冷落了29年期国债,LTCM因此做空30年期同时做多29年期国债,直到两者价差趋同。
LTCM一度笑傲群雄,他们共发现3.8万对类似的差价组合,仅1996年就净赚16亿美元。到1998年给客户超过其资本总量70亿美元三分之一的回报。LTCM像穿上了魔力红舞鞋一发而不可收,直到1998年8月俄罗斯无力偿还令国债交易的疯狂舞曲嘎然而止。金融市场一下丧失了理智,各路资本惊慌出逃。LTCM一直做多相对流动性差的资产、做空相对流动性好的资产来对冲,突然两种头寸同陷泥潭。当其打算解套脱身时,别家早已捷足先溜。LTCM手中头寸实在太大,其出货操作使价格在两个方向同时遭受更大压力。差价组合本应“收敛”,却一反常态被迫“发散”,峰值期间连续数日每天亏损过亿美元。
从高速繁荣到瞬间崩溃,LTCM实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缩影。
稳定催生贪婪,预警实难奏效
自从商品派生出金融市场,监管当局就一直追求稳定,剿杀破坏稳定的因素。毕生从事危机研究的经济学家Minksy指出:危机自然产生。金融稳定本身带来信心泛滥和投资冒险,演变为动荡,直到危机爆发和经济衰退后又重新稳定并开始新一轮循环。
理性实在难以量化。很多预言家早就指出金融体系存在危机,如华尔街著名学者Kaufman、纽约大学教授Roubini等。但市场对其警告充耳不闻。1929年颇负盛名的Warburg说华尔街可能崩溃,却被冠以“破坏美国繁荣”的罪名。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只是众多危机预言家之一。加州大学Eichengreen和罗格斯大学Bordo统计,1973到1997年的24年间共发生过139次金融危机,其中44次在发达国家,而1945到1971年26年间仅38次,可见当代危机翻番。人们举不出因预言而成功预防金融危机的案例,预言只能作为事后评价学术成果的依据。
麻省理工学院Lo教授于2004年设想了雷曼兄弟公司总裁和首席风险官间的对抗。风险官因预见灾难而建议关闭抵押贷款业务,但总裁当场威胁要解雇他,因为竞争对手正不断扩大该业务,且一旦关闭或削减抵押贷款则大批精英也将被挖。风险官提出采取措施对冲风险,总裁反驳说对冲将导致雷曼损失数亿美元!许多企业家称成功缘于“对上帝的恐惧”,但“对上帝的恐惧”正日益被“对上司的恐惧”所取代。
贪婪成为部分机构“金融创新”的动力
金融产品创新的价值原本在于稳定受益、配置资产、引导投资和规避风险,为实体经济供血输液、保驾护航。当经济繁荣和全球化为金融市场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流动性,当通货膨胀、利率下行推动部分银行、保险公司等摒弃传统的、日益收窄的存贷利差,转而追求新的资本扩张模式时,金融创新便以日益超越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的质量加速度畸变和异化。尤其金融帝国美国的科技和创新才能更使这场灾难变本加厉。
最著名的“创新品种”就是直接引发此次危机的CDOs。芝加哥大学教授Rajan称之为“在所有导致经济危机的金融工具中最具破坏性的金融工具之一”。当人们将次贷按揭资产池捆绑转化为CDOs时,金融建模背后的理念便面目全非。当今世界舆论大多认为CDO除了卖钱毫无用处——现金经由按揭偿付进入单一CDO需经过多层过滤,资产被组合成池旨在进行证券化操作,而后被塞进CDO,其中一些还会塞进下一个CDO并如此循环往复。每个CDO来源的相关文本与条件均长篇累牍令人厌烦。一个典型CDO的现金流源头可达数百个——那简直就是留给律师们的天堂。比起期货和期权,这类创新产品的共同特色就是错综复杂眼花缭乱。每个CDO的销售均以其自身的推测为基础,依据就是对未来30年利率及违约率乐观的核心假设和显示该CDO足够牢靠的“压力测试”。奇怪的是所有“压力测试”均未考虑到高达20%的房价下跌“压力”。
这便是这类创新最致命的要害——试图以今天已知的市场价格推导明天的价格,尤其样本中“创新性”地剔除了上世纪30年代全国性房价下跌的背景。其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把CDO更快地卖出去。
贪婪能把科技变为随心所欲的工具
数学模型是预测金融市场的有力工具。然而在不同的使用者手中,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现代金融归根结底与风险度量密切相关。使用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必须“清楚自己的假设所在,从而准确了解哪些可能忽略的风险”。相比之下在CDO中使用者“并不清楚自己忽略了什么,因而也不清楚怎样修正。”
银行使用“在险价值”法(VAR)所制造出来的数据几乎具有同样的破坏性。VAR被认为可以显示金融机构的安全系数。监管者利用VAR来计算银行究竟需要多少资本来预防不测。然而这类估算潜藏着对“尾部风险”的忽视。试想象银行可能的单日损失与盈利范围为一个统计分布,多数时候小赚小赔。偶尔发生大赚大赔。将其绘成图像,便可得到正态分布的著名钟型曲线。通常VAR法会在图上切一条线代表98%或者99%,并以此作为极端损失的衡量指标,意指极端损失的概率为2%或者1%。
然而,尽管正态分布曲线的中央区域——即大部分盈利与损失之所在——近似反映了现实状况,其两个尾部却大有玄机。在金融市场,极端事件普遍得令人吃惊,两端的“小尾巴”其实硕大无朋!根据发明分形理论的数学家Mandelbrot教授计算,倘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真的遵行正态分布,则1916至2003年间其超过3.4%和4.5%的波动分别只有58天和6天,而事实是1001天和366天;本应每30万年才出现一次超过7%的波动,仅仅20世纪就经历了48次。换句话说,用VAR预测日常的、位于正态分布中心的小额损失相当胜任,而预测那些少见却能导致惨重损失的事件却毫无用处。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Acemoglu说:现代金融正在给这个“小尾巴”增肥。当交易掉外汇、利率等所有特定风险后,投资组合似乎更安全了。可事实上只是调换了日常与异常的风险。统计分布中央的可预测风险显得少了,那些不可观测的尾部风险却在上升。交易商与经纪只关心自己能否在更低的风险水平上赚取可观的利润,而真正的风险却被部分掩盖起来。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Phelps强烈认为“对一个如此复杂的系统做到如此细致并如此令人惊讶的准确了解是不可想象的……要想满足此条件的信息要求已经超出了我们搜集信息的能力。”
科技本是客观和严密的,可到了贪婪的手中就被任意肢解和扭曲,改造成满足贪婪目标的“得心应手”工具。
“市场需求”成为贪婪的理由
不少“金融创新”产品(如信用违约互换)实质是典型的赌局。购买者向出售者支付一定费用,而一旦出现信用类事件,如石油价格下跌或房贷者不能按时交纳抵押款等,购买者就能因此获利。“收支等量”亦即“零和游戏”,理论上“收支等量”,但损益双方后果则不能相抵。赌注越高,交易对手风险越大。美国国际集团AIG一度是全球最大保险公司,因其巨额投注失利,政府被迫拯救。一旦AIG破产,则赌局另一方也会面临严峻的风险。虽然整个市场收支等量,但局部不平衡好比一根梁柱承重超载,同样会令整幢大厦轰然坍塌。
华尔街流行一句格言:产品好坏关键看顾客是否为之掏钱。换句话说,有市场需求就有存在价值。一些国际知名专家学者认为之所以美国历次危机不仅没有停止金融衍生品的发展,是因为“金融需求持续存在……市场上有这么多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是虚玩,是因为存在真实需求。那种认为除了基础性证券市场之外一切衍生品都是泡沫的想法,是不了解金融市场。”
然而CDOs这类衍生产品的“市场需求”,归根结底是人为超前制造出来的——政府为了政绩声称让人人拥有住房,房地产商迫切希望住房金融化从而拉升房价,银行希望叫花子也来按揭但又要确保还贷,于是虚拟能满足贷款购房又规避风险的“金融创新”产品才得以大行其道。
“恐惧”的危害绝不低于“贪婪”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Buiter早就说过:“金融天生具有不稳定性,但这是必不可少的。金融的不稳定性随时会引起恐惧。”
为保证交易双方兑现承诺,投资者会采用各种防范措施。如法规细化、资产价值准确描述、引入押金、保证金和合同、聘请专家信用评估等。金融系统效率越高,贪婪与恐慌传播速度就越快。一旦投资者失去信心撤资离场,流动性和信用一夜之间就变成稀缺资源,代之以极具破坏性的不确定性。自雷曼破产以来,出于对破产或国家救市可能导致血本无归的恐惧,银行被突然要求加大资本资产比。该比率过去几十年间都很稳定,不到账面价值的10%,不久前美国对银行业“压力测试”的初步结果,花旗和美银均不及格,其中美银面临数十亿美元的缺口。受此打击亚太股市加速下挫,欧洲股市一路狂泻。银行股再次成为下跌“重灾区”。英国遭遇了19世纪70年代至今首次银行挤兑。美国则不断“救援”疲于奔命。
CDO大幅贬值使恐惧笼罩整个信用衍生品市场。众多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巨亏,近半的对冲基金可能黯然退市。发行和管理衍生品的公司股价下跌,引发投资者持股的惊慌。百年历史的世界三家顶尖投行雷曼、美林、贝尔斯登香消玉殒,90余家银行进入FDIC“问题名单”,39家银行破产,花旗银行资产缩水近98%,汇丰银行利润骤降七成,道琼斯指数一度创下6000新低,缩水超过高峰期的50%,金融时报指数创6年新低,日经225指数跌至26年最低,全球金融资产缩水50万亿美元。全球金融体系濒临系统性崩溃边缘。
恐惧从金融向实体经济蔓延,世贸组织预计2009年全球贸易额将下降10%,世界经济整体下滑0.5%—1.0%,60年来首次负增长,全球人均收入近20年来首次下降。
医治贪婪和恐惧没有特效药
贪婪与恐惧是金融市场的永恒话题,代表着市场的两极心态。本次危机充分证明我们对贪婪和恐惧的能量、危害和表现形式、演变路径的认识还远没有到位。
金融市场中理性和乐观随机产生非理性,从而使危机常态化。金融市场永远在贪婪与恐惧中运转。监管只能限制贪婪与恐惧,却无法战胜人性,因为监管者也是人。
正由于人性无法被战胜,所以又只能加强监管,但金融创新永远不可能叫停。市场最终可用套利工具攻下监管者布防最严密的城堡。今天我们站在衰退的低谷,很难想象当初怎么就视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的疯狂敛财为正常。将来有一天我们同样难以理解今日人们为何如此恐惧?为何不在如此低位买入股票、黄金或公司债券?为何没看见美元持续下跌……届时贪婪又将再次俘虏我们的灵魂。
前美联储理事Mishkin称金融为“经济体系的大脑”,这固然体现了金融的力量和重要性,也隐含着金融的复杂和脆弱性。
我们重新发现了一些古老的真理:人并不总是理性的,市场法规和人性道德并不完美,金融市场并不总能自我修正。贪婪是危机的病根,恐惧是暴发的病症。金融危机尚无法根治,只能先治标,后治本……
上一篇:利弗莫尔的投机传奇及启示
下一篇:人责钓者我却责鱼